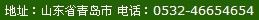|
一印章方面 (一)『内府图书之印』 在《临韦偃牧放图》的画面中,有一款印章『内府图书之印』有明显的问题: 其一,它的印章盖到了朱元璋题跋的字的上面。 『内府图书之印』与『御书』葫芦印、双龙印、『宣龢』连珠印、『政和』长印、『宣和』长印以及『政龢』连珠印一起组成『宣和七玺』。『宣和七玺』中的每个印玺都有它固定的钤盖位置。『内府图书之印』的标准盖章的位置是在纸尾的中间位置,此卷《临韦偃牧放图》中的『内府图书之印』的盖章位置是没有问题的,而问题出在了印章盖到了朱元璋题跋的字上面了,『内府图书之印』是宋徽宗时期内府的官方印章,而朱元璋是明朝的皇帝,在字迹上能明显地看到印章的红色痕迹,所以应该是后来盖上去的,因此『内府图书之印』是伪印。 其二,印文的纹样与标准的纹样有明显的区别。 其中,印章中『啚』字上面的『口』和下边的『回』是通过中间『十』的竖画连在一起的,而标准的『内府图书之印』如杜牧《张好好诗》卷,怀素《论书帖》,张旭《古诗四帖》中的『内府图书之印』,『图』字中的『啚』上面的『口』和下边的『回』之间却是一个『』,中间的一竖并未出头连接到『回』字,其他的标准『内府图书之印』也是如此,所以李公麟此卷中『内府图书之印』不是真印。 (二)『政龢』连珠印 『政龢』连珠印作为宣和七玺中的一玺,它的位置是在后隔水与尾纸的接缝处,上下居中,左右在尾纸和后隔水各占一半。此卷《临韦偃牧放图》中的『政龢』连珠印在位置上是没有问题的,它的问题在于印文的字形与标准『政龢』连珠印如《张好好诗》卷中的『政龢』连珠印,《平复帖》中的『政龢』连珠印,有明显的不同。 其一,在《临韦偃牧放图》中『政龢』连珠印的『政』字第一笔横画接左边框,左下竖折为方折形,而标准『政龢』连珠印的『政』字不仅第一笔不接左边框,且左下竖折部分为圆弧形,这是第一个差别。其二,此卷中『政龢』连珠印的『龢』字,左边『龠』结构相对松散,中间的三个『口』已简化为两个,而标准『政龢』连珠印左边『龠』的结构则比较紧凑,中间仍是三个『口』,这是第二个差别。 然而,如果以尾纸和后隔水的接缝为界,把此卷『政龢』连珠印中『政』『龢』二字的右半部分却与标准『政龢』连珠印的右半部分比较一下,却可以发现它们又完全地吻合,这也可能说明右边部分可能是真印。对此卷中『政龢』连珠印的左右矛盾,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后隔水上的印迹是标准印迹,而左边原来的尾纸上的标准印迹因重新装裱而随尾纸一起被裁去,重新换一张尾纸后补盖了左半部分。 二题跋 在此卷《临韦偃牧放图》画芯卷首的上面,有两行小篆墨迹:『臣李公麟奉勅摹韦偃牧放图』,因此而说此卷是李公麟奉皇帝之命而临摹的作品。在此有一点疑虑,就是以李公麟的线条功夫和造型能力,书法也是相当不错的,这两行小篆写的柔弱无力,不似李公麟的风格。 李公麟是线描高手,线条功夫极为深厚,这在其画作中能看得出来,虽然他以画闻名,但是李公麟在当时也有书名,董史《皇宋书录》中即有李公麟在内。至于小篆,在清朝之前,基本上都受到『玉箸篆』式的规范,要求字形端正,圆起圆收,线条粗细一致且光滑劲挺,富于张力。宋朝尤尊『二李』(李斯、李阳冰)篆法,因为拘于『二李』之法,相较前人而言没有很大的超越,故而我们常以为宋代篆书衰落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,在宋代,上至皇帝,下至贫民,皆有善篆书者,至于士大夫阶层,如徐铉、章友直以及黄庭坚等皆善篆书,功力颇深。 以李公麟的线条功夫和造型能力,其小篆也应是结字匀称端正,线条光滑劲挺,富有弹性。而观此两行小篆,不仅线条羸弱,结字也不太好。如图七,除了个别字以及部分字的部分笔画以外,整个两行小篆线条粗细不一,毫无劲挺圆滑、富有弹性可言。在字形上,『奉』字上部和『勅』左边,都有明显的倾斜或重心偏移,『韦』字太小,『牧』字又太松散,『放』字左右不协调,而在用笔上,几乎每个字都有问题,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弯折处,很多地方变圆转为方折,且显得僵直。因为这些问题,所以我认为这两行小篆也存在问题。 卷首自题『臣李公麟奉勅摹韦偃牧放图』,很多人认为,李公麟是奉徽宗皇帝之勅,然而李公麟早在元符三年就因病痹致仕,归老龙眠山,当时徽宗还未即位,如何颁布勅命?况且李公麟晚年已不再画马,且龙眠山距汴京有千里之遥,徽宗下旨令李公麟以老弱之躯去汴京临摹一幅《牧放图》,似乎太不合乎情理。作者闫慧《荣宝斋》年5月刊《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印款辨伪》 因此,通过以上具体的分析,《临韦偃牧放图》上的印款应不是真迹,而是一幅伪托之作。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13801256026.com/pgsp/pgsp/8658.html |
当前位置: 印章 >临韦偃牧放图上的印款究竟是真是假文
时间:2025/1/15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苏轼木石图经手数代藏家珍藏,今天价值
- 下一篇文章: 古人的书简印和斋馆别号印谈艺录